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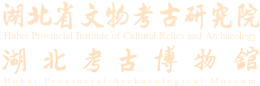
推开九里岗考古工地整理室的门,热熔胶枪的嗡鸣与陶片碰撞的脆响交织成独特的奏鸣曲。队员们指尖抚过一片夹炭陶的断口——黑色的炭挥发痕迹在胎体中若隐若现,那是大溪先民为防止陶器开裂掺入的“秘方”。陶衣剥落处露出的蜂窝状孔隙,恍如远古陶轮转动的年轮。

“这片酱釉罐口沿内折角度15度,典型二期特征。”
“灰坑H141出土的夹蚌红陶,胎体比早段致密。”
低语声在标本架间流淌。考古队员手持卡尺,测量陶片厚度;放大镜下,指甲盖大小的陶衣残片显露出细密的篦划纹——那是先民制陶时用芦苇杆划出的装饰线,如今成了判断器物年代的“指纹”。

分类台上,陶片按质地(泥质、夹炭、夹砂、夹蚌)、釉色(酱、红、灰、黑)、器型(釜、罐、盆、钵)被归入一个个塑料筐。一片陶盆残片边缘的热熔胶正在凝固,它曾因埋藏环境影响裂成多片,而今正在胶体牵引下重现其恢弘轮廓······

另一边工作台,一件陶器器盖的线图正被赋予生命。考古队员手持铅笔沿着比例尺游走,笔尖与硫酸纸摩擦的沙沙声,仿佛在复刻先民制陶时的刮削节奏。

考古绘图,器物的第一次“身份证照”,是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考古绘图是对遗迹或者文物按比例二维复原。它与文字记录、照相记录相辅相成,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为直观的资料。
今天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来更高效地完成绘图工作。然而在大多数考古工地上,仍然坚持手绘。这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有时候可能是由于考古发掘现场本身并不一定支持高科技设备的运行,为了完成现场的第一次采样,考古工作者往往选择了手绘来完成这项工作。

此外,技术也并非万能。一般来说,一处遗址的整体结构、内部情况难以通过拍照直观呈现,出土文物也可能因为刻痕细微、锈蚀、埋藏环境等因素导致纹饰不清晰,而这些正是考古研究中判断文物年代、分析文化源流的关键信息,所以必然使用传统的方式来保证准确性。
在九里岗,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一天天地坚持着,带领新一代的考古人,一笔一画,描摹陶片纹路,镌刻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文明······
六千年前某个清晨,一位母亲将掺了稻壳的陶土摔打成坯;正午时分,陶工在慢轮上修整罐颈的折角;暮色里,新烧的陶盆在聚落炊烟中盛满粟粥。而今,那些指尖的温度、轮盘的离心力、窑火的爆裂声,都封存在九里岗的陶片矩阵中,等待被考古学的光锥重新照亮······